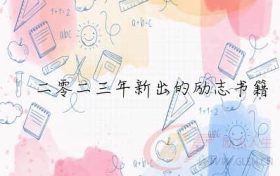文/松劲儿
偏执的觉得,东北或说黑龙江的文化底蕴是比力弱的,全部地域的文化空气是不怎样好的,也较少有本籍龙江或说龙江培养起来的文化大师。即便是当下,单就作家来讲,我可以或许数得出名字的,仿佛真没几个,读过作品而且有再读一次愿望的,也没几个。其实,说真话,这会儿,以上两个“几个”,我是一个也想不起来的。具体到女作家,我所知道的,张抗抗是生于杭州的,知青上山下乡来到黑龙江,后来又留在了黑龙江。迟子建是土生土长的龙江人?她那篇记念亡夫的文章,读来很是使人动容。铁凝性情像东北的,具体没考据过,仿佛也没读过。别说,我能想到的,活着的作家,跟黑龙江沾边的,还真是女作家多于男作家。
糊口在松花江干,早听过萧红的名字,也知道呼兰河养育了她。只是从未造访过萧红故宅,也从未读过萧红的文字。那日找到一本萧红的文集,看了几篇她的文章。很熟习的感受。由于,故事年夜多产生在那片黑地盘,固然是很多年之前的工作了,但那些在卑劣的天然情况和社会情况中疾苦求保存的人们,也能够称得上是我的乡亲长者。理解。让我不测的是,从萧红的文字中,看不到几多女性的陈迹。一般的,性别是会影响到文字的,言为心声,想领会一小我,比力好的一个方式是经由过程他的文字嘛。由于女性的细腻,文字常常缱绻,场景相对较小,一读就可以感受出来。也许是由于阿谁外敌入侵的年月,不管男女,都要像汉子一样去战役。也许是由于那黑土隆冬锤炼了萧红,使她视野像冬风那样豪放,文字像冰雪那样坦荡。而冬季里的阳光,暖和了她那颗心,使她对通俗平易近众的苦痛,有切肤的感知。呵,看,我的文字,较着是个女子所作,不豪宕,小家子气。看《存亡场》,看萧红描述的阿谁年月,老农的糊口,我不知道心里是为他们的醒觉赞叹仍是为他们的蒙昧愤闷,只能说,他们挣扎在社会的最最底层,在世,是很不轻易的。汗青,常常是类似的。
带着豪情看事物,动身点有问题,欠好,但我却难以解脱。说严重点,若是没有豪情了,我可能也写不出来如许的漫笔文字了。也许,我可以很理性,经由过程思惟的练习,可以很理性地写论文,但,今朝,我做不到,也不想做。我是想说,东北抗战,是很不轻易的。固然,哪的抗战都是不轻易的。我还想说,抗战不是十年夜元帅或说某些将领的,而是每个介入抗战的通俗平易近众的,哪怕他是个不起眼的小鬼,哪怕他只给过路的小鬼抱去一捆草。战争,抗战,是每个通俗苍生的。
八年抗战,不算短。其实很多人不知道,东北的抗战,进行了十几年(年夜概是十四年)。火烤胸前暖,风吹背后寒。也许带着一点革命浪漫主义,或说是宣扬鼓舞将士的需要,现实环境,多是我们没法想象的艰辛。有乐趣的,也许可以在有雪的季候,吃得饱饱的,裹得严严实实的,去郊外走上半天。像“重走抗联路”的人一样,稍稍感触感染一下。想昔时,他们是吃不饱穿不暖的,雪窖冰天里睡在野外,还要随时被全副武装的鬼子追杀。隆冬尾月,活活冻失落脚,都不是新颖事。像戏曲中杨子荣那样骑着年夜马,披着年夜氅,是比力有想象力的。不可,我的想象力很匮乏,我想象不出来,他们的战争糊口。我想象不出来,他们如何凭着朴实的打跑鬼子的信心,在没有上级撑持,在很少能找到老乡补给的东北年夜地上,独自对峙了十几年。一次,有幸听到抗联老兵士李敏的陈述,九十多岁高龄的白叟了,瘦瘦的,精力头儿实足,真的,比我们二三十岁的年夜姑娘小伙子有精力劲儿多了。讲到某处,现场就高唱昔时同志们唱过的歌曲,依然那末有气力,振奋人心。从李敏白叟的身上,你可以或许感触感染到,阿谁年月的人们,那些昔时的抗联兵士们,他们的崇奉与对峙,他们是有精力的。向那些有血性有对峙的东北汉子,致敬!
关于抗联的这个话题,好久之前就想写了,但老是感觉火候不到。今天,写到萧红,又勾起了它。但我发现,我仍是把握不了,写不出来我想写的,那些心里里仍不逼真不清楚的工具。头儿已开了,暂且,继续写下几点似清楚的记忆吧。
在老家,屯中春秋最长的白叟,曾介入过抗战。具体怎样介入,是介入的抗联,仍是介入的正规军,是给某个小首长办事了,仍是在后方干事了,不清晰。他知道我爸爸的爷爷家的情形,早些年跟我的姥爷讲过。是以,我所传闻的关于家族中更老一些的工作,口口相传下来,就不知道是传自哪里了,也无从验证其真实性了,看成一个故事听吧。
昔时,平易近不聊生,很多多少人家都活不下去了。祖上的一名父亲,年夜概是爷爷的爷爷,带着几个孩子走了,家中留下了一个或几个吧。孩子应当也就是十几岁,此中仿佛有个叫小五子的。过了不知是几个月仍是几年,一个夜晚,这位父亲鬼鬼祟祟的回家来看了一眼,走之前告知家里的人,若是有人问起,不要说我们回来过,“你们就当我们死了吧,就当没有我们这几小我。”感受,他们是加入了抗联。有其他的证据表白,他们或更精确地说,他们当中有人,确切是抗联。不会有人再记得他们是谁了,生命真的如草芥吗?像《白鹿原》中的白灵,还算荣幸的吧,那末多为革命牺牲的人中,她的儿子还能在几十年以后,知道本身母亲灭亡前后的工作,知道本身的母亲是谁。而其他更多的人呢?那都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,每小我背后,都是一个家庭乃至是一个家族。甚么时辰,我们可以或许从心里深处,当真悼念一下,作为个别的,战争中逝去的生命。是那些可以感知的通俗人,铸就了我们平易近族新的长城。
前两年,崔永元做了一件应被汗青记住的工作——记实通俗抗战白叟讲述的战争。那是真实的战争,那是平易近众书写的汗青。遗憾的是,仿佛并没有引发甚么深远的社会反应。悲痛的是,我至今都不曾去具体的看一看。真的由于我们愿意遗忘?